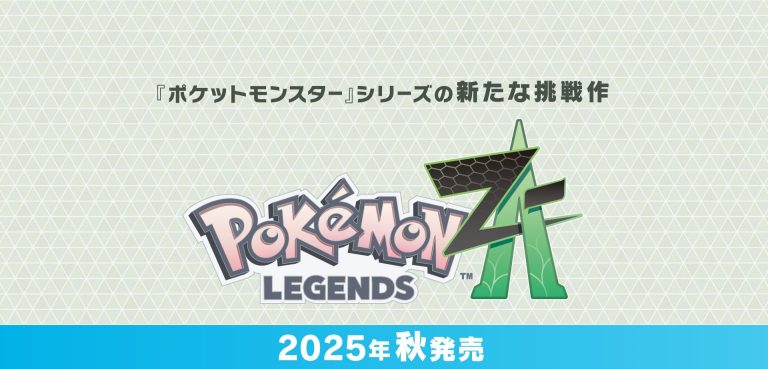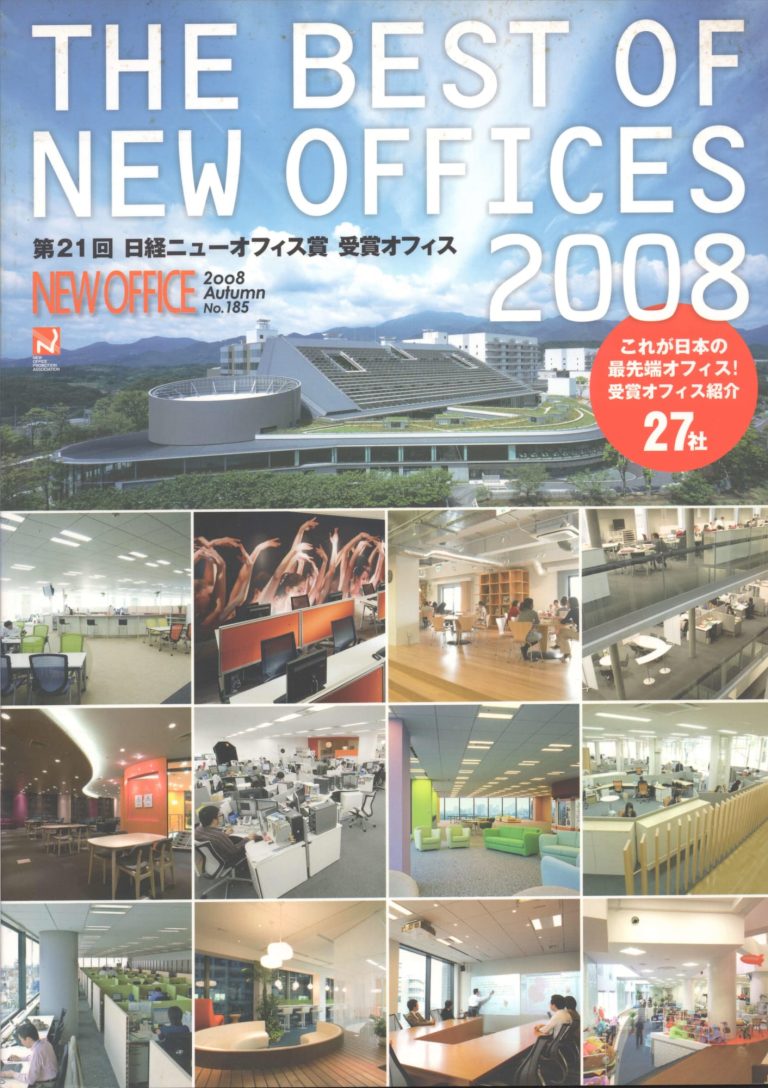原文:https://news.denfaminicogamer.jp/projectbook/xevious
本文基于2022年6月24日在B站上发布的一篇访谈——ʚ宝可梦采访翻译ɞ 2016年田尻智 杉森建与《铁板阵》之父远藤雅伸的高能会谈,译者为Yumi的宝可梦调查小队。早年也读过这篇访谈,当时也因为篇幅而搁置了翻译的计划,如今能通过校对的身份参与实属荣幸。
而另一方面,尽管文章的翻译已经完成,但对此的挖掘还远没有结束,Yumi的视频——“梦幻”事件真的是巧合吗?宝可梦之父田尻智来告诉你答案!以讲述田尻智与铁板阵结缘并走上游戏制作人道路的背景故事的角度说明了梦幻事件的诞生很可能受到了街机时代特色的“彩蛋/bug”与“都市传说”现象的影响,即便事件的发生只是巧合,也找到了因果的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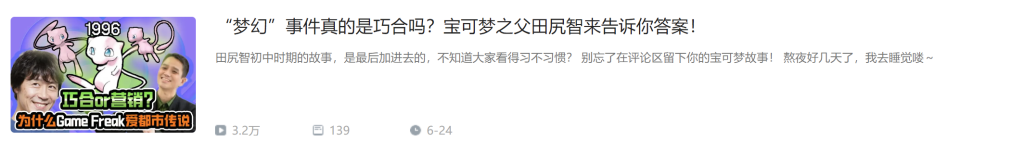
本文则是专注于从现今的眼光再看田尻智这篇采访中的一些有趣的点,由于学业原因时间有限,挖掘并没有太深入,就当是抛砖引玉一番吧。

1.”GAME FREAK的街机出身”
原文的第五章节提到了GAME FREAK班底的“街机出身”和初代的“街机感”(开场的感觉)
5.Game Freak是街机出身?
──某种意义上,虽然同样是RPG,可以说堀井雄二与中村光一做的《勇者斗恶龙》来自电脑游戏的文脉,而《宝可梦》来自街机游戏的文脉是吗?
田尻:
我是这么想的。
远藤:
虽然说成“街机游戏的文脉”不太严谨,但它的口味绝对是偏向街机的。
虽然这段故事(指田尻是街机厅高手并且也是因为做街机攻略而名声大噪)早有耳闻,但看到这段自述时还是有点眼前一亮的感觉。

宝可梦社群里一直有个话题——什么是宝味?/某某有没有宝味?
我们常常会在贴吧,NGA,或者微博评论区里遇到相关的讨论,或者说争论。近年来比较多的集中于宝可梦设计,但总体来说包含了对于音乐,剧情,美术,画面,对话等方面。换句话说,只要是宝可梦系列中的一个突出特色,与后续世代的差异都能成为“宝味”的一个评判点。从某种意义上,宝可梦作品的创作可以被概括为如何将现实中的元素转化到已有的宝可梦世界观中去。既然如此,即便是同一个人/一批人,面对不同素材的转化都是存在差异的,这一点即便在早期的作品,即宝味定义者or引领者,的内部就有体现,而在宝可梦正统作品走出日本,迈向全球取材后,制作人离开自己熟悉的几十年生活环境在有限的周期内去寻找适合被转化的事物自然就意味着更高的难度。
田尻智的童年是拿着捉虫网在田野捉虫交换的夏天,无拘无束的少年与各种各样的生物相遇,增田顺一的童年是前往九州老家度过暑假,舟游海滩边的冒险,前往洞窟探秘,望着多变的天气想象着远古的故事。这些基于制作人现实生活经历的创作在世界观开创,拓展和完善一块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少年与奇幻生物相遇的冒险,带有大人式说教观念的反派,基于自然和人文的神话生物,显然将自己最深刻的体验毫无保留地转换成宝可梦世界是最高效且具有感染力的。
因此,一个比较明显的矛盾是,宝可梦作品所对应的世界观需要一定的生活感,但制作人在海外当地生活的经历断断续续可能只有半年,几个月甚至更少,因此就存在着同一批人对于不同素材转换能力差异的这一事实,一些日积月累的生活感触有时很可能是制作一款“活灵活现”世界观作品的关键,假如火候不够就被拉回来开始制作,不免会造成一些“宝味”的偏差。
举一个正面的例子:有一回在twi上看到一件趣事:佐藤被宝友艾特说由她作曲的帆巴市的BGM已经被越南当作了婚礼配乐,但她回应说自己其实并没有主动去听这类曲子而后去模仿着创作。事实则是她在常去泰国餐馆中经常听到了这类旋律,耳濡之下就有灵感。但需要认识到的是误打误撞之外,自然也意味着可能会出现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机会去浸染于当地环境而发挥有所不足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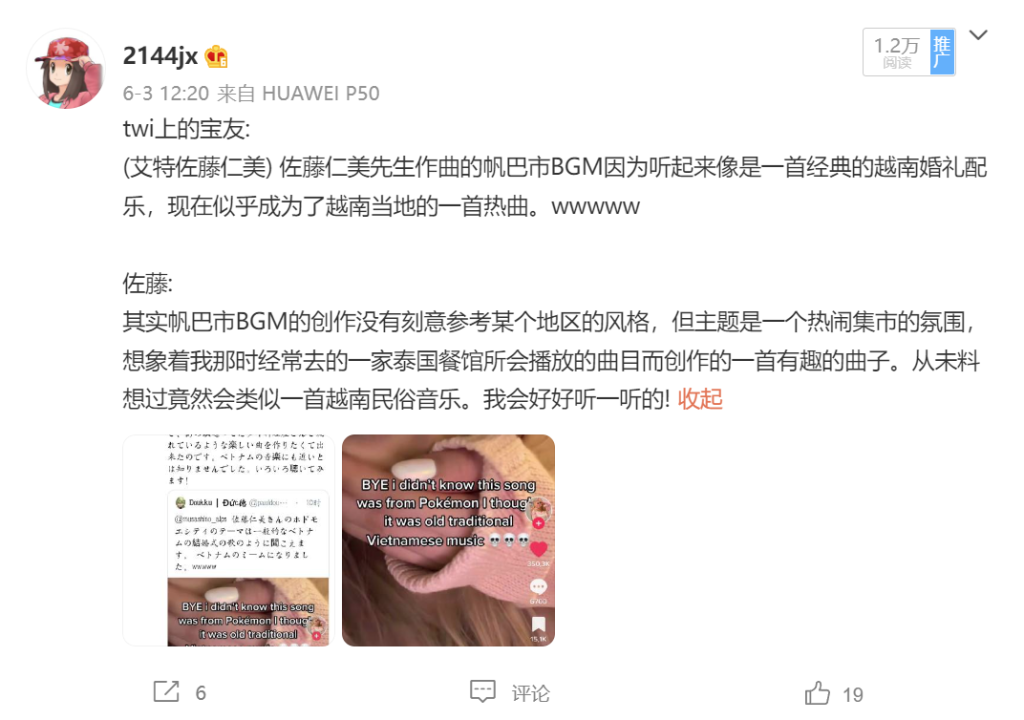
而对于这个矛盾,我认为GAME FREAK其中一个的应对策略是,拓展宝味的定义:把一些要素留在过去的作品,在新环境中夹杂一些原有世代风格的内容,同时也在新世代大胆地采用一些新思路去做设计。就比如黑白的创作内核包含着对标初代的全新宝可梦,同时也加入了不少运用初代公式创作的宝可梦,以及浓郁的亚洲文化元素。不过其实这话的逻辑也会理解为:“抛弃原有的一部分宝味,去定义新的宝味。”,犹如“忒休斯之船”(一艘船全部的零件都被替换成新的后还能被当成原本的船吗?),虽然能被理解成拓展宝味,同时不也是和原有的宝味渐行渐远的意味呢?
是的,但也不是。
这取决于最终作品呈现的效果,以及作为评判者的玩家的个人接受度,而一旦涉及到个人,这个问题就不太可能有明确的界定标准,由此也造成了无限的争论。在以往,负面评价一般会有社群内部去消化兜底,大家都会彼此认同对方的不满,同时也认识到一部分不满可能来自于自己的偏好,不必强加到普遍层面去批判。而近年来风评的下降和因赶工展现出的仓促和技术力储备不足使得玩家(以及路人)对制作组的产出和一举一动都普遍持怀疑态度,因此在国内就演变成了遍地开战的场面,有时候很难说现今暴露出的问题在之前世代没有,但也确实到了这么一个人人评说“宝味”的时代。
而就相对“客观”的层面来看,游戏的画风,要素,人物设计之类的其实都不应该影响玩家对作品正不正统(宝不宝)的评价,只要内核还是围绕着宝可梦的捕捉,培育,交换,战斗的四大模式,那就是最浓的宝味,其余都是辅助让大家接受这套内核的元素,只要足够好,玩家自然会认同这也成为正统作品的一部分。就像大家都仍同《塞尔达传说》系列的内核就是解谜和冒险,无论画风改成什么样,在把握了这两个前提下,就会被当成《塞尔达传说》系列本篇。
不知不觉聊了一些看起来偏题的内容,不过如果一上来就聊本节的“街机感”和“宝味”的关系,也稍显了有点空中楼阁。宝味的话题总是值得一聊,而对于本节的“街机感”以及GAME FREAK班底的“街机”出身,如果将其视为过去宝味(醍醐味)的一部分的话,应该怎样看待这一部分在宝可梦系列中的存续呢?
采访文中提到众人的决定是“用街机厅的体验制作不一样的游戏”,而“街机厅的体验”又是什么呢?文中杉森对街机感的说明是:
杉森建:
“简单来说,游戏会突然开始这点吧。我们不会加入漫长的说明。”
“采访人:确实,电脑的冒险游戏,会从内容说明开始。”
“我们想要玩家争分夺秒地开始操作,但是那些游戏感觉还是会让玩家先读一通文字。这是个重要的区别。”
开场不需过多说明,即需要简单上手,在画面呈现的内容上引导玩家的一切行为;突然开始,即读档不折磨,也迎合了掌机随开随玩的特性。
那么仔细一想,第八世代不也是这样嘛?这一部分的核心设计确实能够追根溯源到街机,并且街机按键少与掌机也有天然的契合度,使得初代开发众对家用机以及GB的玩法构思得心应手,针对硬件本身去进行开发也很长一段时间是GAME FREAK的拿手好戏,其中一个冷知识是——GAME BOY CAMERA的开发商正是GAME FREAK,而阅过千奇百怪的街机的田尻众在掌机平台上开发的诸多新可能性或许也是为了还原街机的这种定制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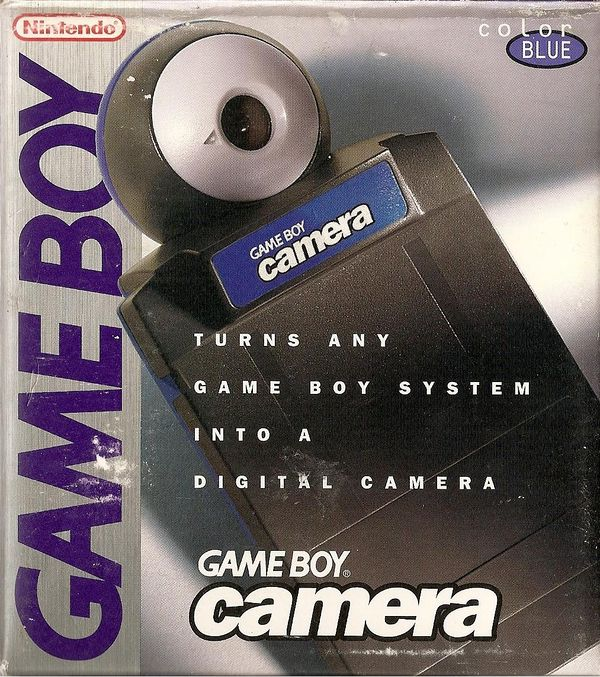
那么除此之外的“街机感”与“街机出身”又体现在何处呢?
或许就要重提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GAME FREAK的技术力”,田尻众游玩街机的时代,一般是80年代左右,那个时候的街机因为硬件原因还没到卷画面的时期,因此更加注重玩法设计。由此对于田尻众来说,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种重玩法,轻画面的观念。加上GAME FREAK本身是玩家组成的同人志社团,编程基本靠自学,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技术力中下游的开局,而后的成功也基本让他们确信,玩法设计和要素完备性远高于画面表现力的提升。
对此田尻的漫画中也有点评↓

同样的,在法米通的GAME FREAK30周年纪念访谈中,先辈也提到了他明确意识到了GAME FREAK虽然在玩法上进取之外,技术上一直存在短板,其原因在于他们对于技术追求还仅仅是当一些想法的实现/新的表现力需要用到对应技术时才去尝试升级,而非先升级到最新的技术然后再看能否制作出对应等级的作品。

虽然这部分标题上用了更引入注目的“技术”,但实际上我想表达的是传承下来的是对玩法的追求,很难有一个回合制游戏能在每三年做出一些数值机制上的重大调整,并且维持一个十万人参与的比赛项目,更不用说在三年也不间断地产出作品,而没有使玩家感到无比的厌倦。这部分内容先辈也在上图的采访中有所提及,新人会被组织去探讨初代在作品上成功的原因,这个活动称为“赤绿研修”,目的就是为了让新社员了解宝可梦的成功来自于对于玩法的追求,这也是所谓“街机出身”以及“街机感”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不管怎么说,“街机感”这个思路对于研究初代的创作历程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思路,而如果把由街机文化所孕育的“都市传说”和“找彩蛋”也视作“街机感”的一部分,其实Yumi视频所讲述的脉络也能纳入本节中,那么初代无疑也是这种“街机感”最大的受益者。
2.“要做新的游戏,就要创造新的动词”
8.日本的创作者靠的是“概念”
──田尻在《新游戏设计》中不也写过,“要做新的游戏,就要创造新的动词”吗?比如,《Quinty》来自“掀开”一词。这就是概念主导吧。
“做新的游戏,就要创造新的动词。”,其实上文中讨论的街机感时就想引出这句话了。这在游戏制作中无疑是一种根本性的创造。用物理的角度来看,我们管这个叫做“第一性原理”,就是用物体作用的最基本规律(库仑定律等相互作用)再加上已知的物理常数去计算量子力学体系中相对复杂的情况。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出发,为主角构想一个全新的动词,即交互模式,随后围绕这个交互模式去创作,所诞生的无疑是一款前所未有的新游戏。即便后续方法论上有取他山之石,但内核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也无须担心别人指责抄袭之类的琐事,因为此时的你是真正的创造者。
田尻对这一观点的践行正是从他的第一款游戏《Quinty》就开始了。文中也提到了“掀开”一词,主角通过掀开面板来攻击敌人,掀开面板来获取星星和特殊道具,在不断移动和掀开中消灭所有敌人后通关。玩家与敌人和环境的全部交互就在于“掀开”一词,对于这个动作的一始而终成为了田尻对自己第一款游戏的设计要求。加上不错的关卡设计和创意,使得这款游戏一举成为了名作&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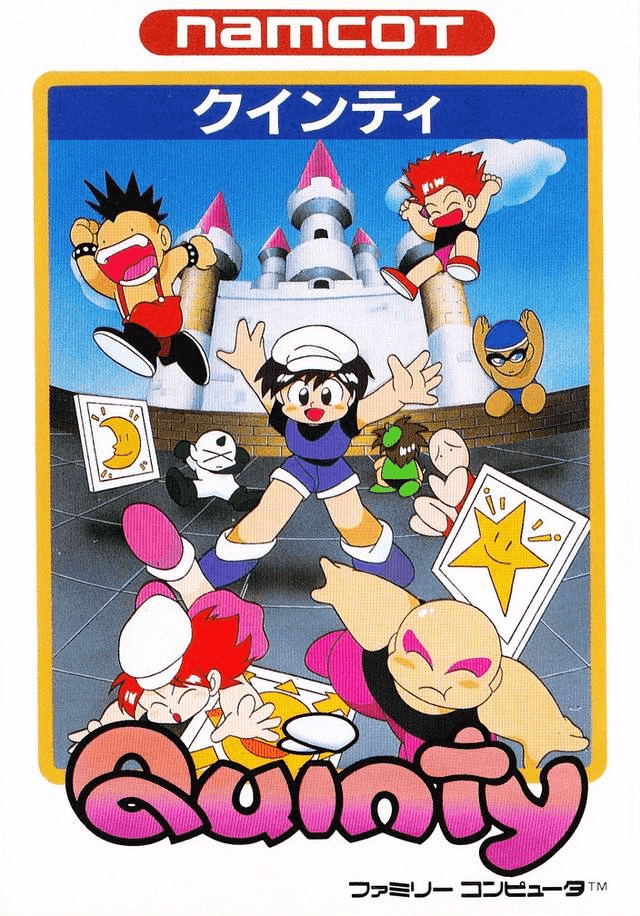
而后田尻也陆陆续续用这套方法论去制作了其他的游戏,比如利用电流脉冲移动和攻击的脉冲超人,对(猴子)角色行动编程通关的《バザールでござーるのゲームでござーる》(类似梦游先生,当然也有自家做的类似机制的前身《马力欧与瓦力欧》),横版加SRPG的青龙传等等。虽然其中的设计和打磨有好有坏,但基本都能被玩家一眼or一上手就概括出一个主要机制和玩法分类,并且散发出“好像有点意思啊”的气息。而采访中提到的《螺旋破坏者 轰振钻子》则是这个理念运用的典型,用一个“钻”字贯穿了整个游戏,不仅是普通的攻击和道具收集,对于钻头钻速的玩法开发(利用一些转速转换成跳跃的初始动能,以及进行反向跳跃),正转反转做出差分设计都让人眼前一亮,再加上本家成熟的GBA美术和关卡设计能力,因此也成为了备受媒体好评的GAME FREAK非宝可梦系列的名作。

如果按照“做新的游戏,就要创造新的动词。”这句话对田尻所有作品进行解读,宝可梦系列的成功可能也源自对“捕捉”,“培育”,“交换”,“战斗”四个动词的开创和交织,因此成为了宠物收集模式中雷打不动的王者。游戏的一切与此相关,一切的乐趣也源自于此。
虽然总是被“调侃”大不如前,但如今的GAME FREAK确确实实没有把这句话给忘了,维护宝可梦系列的根基(四个动词),并且用这个理念在原有捕捉基础上,创作出了“投掷”这个动词,为宝可梦系列注入的全新的活力。虽然只是第一次尝试制作3D的带动作属性的游戏,但依然能一举获得玩家的压倒性好评,无疑是再一次体现这个方法论的魅力。
关于LA玩法的解析我已经专门写了一篇长文,没想到这次竟然又发现了一条脉络,GAME FREAK在这方面总是能超出我的预料。
不过,也需要认识到这个方法论的极限,LA也并非是一个完美的作品,即便是旷野之息,在激情冒险了数十小时后也会突然感到乏味。基于“投掷”体系,LA中给予玩家不断新鲜感的核心是地图中待发现的宝可梦。一旦单次汇报周期中发现新宝可梦的数量锐减,甚至只是在完成已捕捉宝可梦的课题后,冒险的体验就会对应打折扣,在交互机制不再增多(没有每次开图送的交通工具和等级上升后的精灵球&道具解锁)的情况下,增加宝可梦或许也只能满足一部分还没有乏(对这套机制非常喜爱)的玩家继续探索的需求,对应游戏本体的体验来说的提升已经并不大。一个新的“动词”能带来美好的全新体验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饱腹感,因此田尻的游戏也很少出续作。
(或许是暴言)我认为LA目前的体量来说是刚好能被“投掷”一词所撑起来的量,如果将其视作宝可梦系列进化的一个节点,试图在这个基础上再做突破而非仅仅按照这个模板去开发其余世代的传说作品,或许得再构思一个新动词与此交相辉映。
2.plus 难度设计
最后一节本来是想再借远藤先生说的“游戏的难易度,不是游戏的本质” 再聊一下宝可梦游戏中难度的问题,但兜兜转转感觉目前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意,基本都是过去几篇微博中所阐述过的,就贴出来整理一下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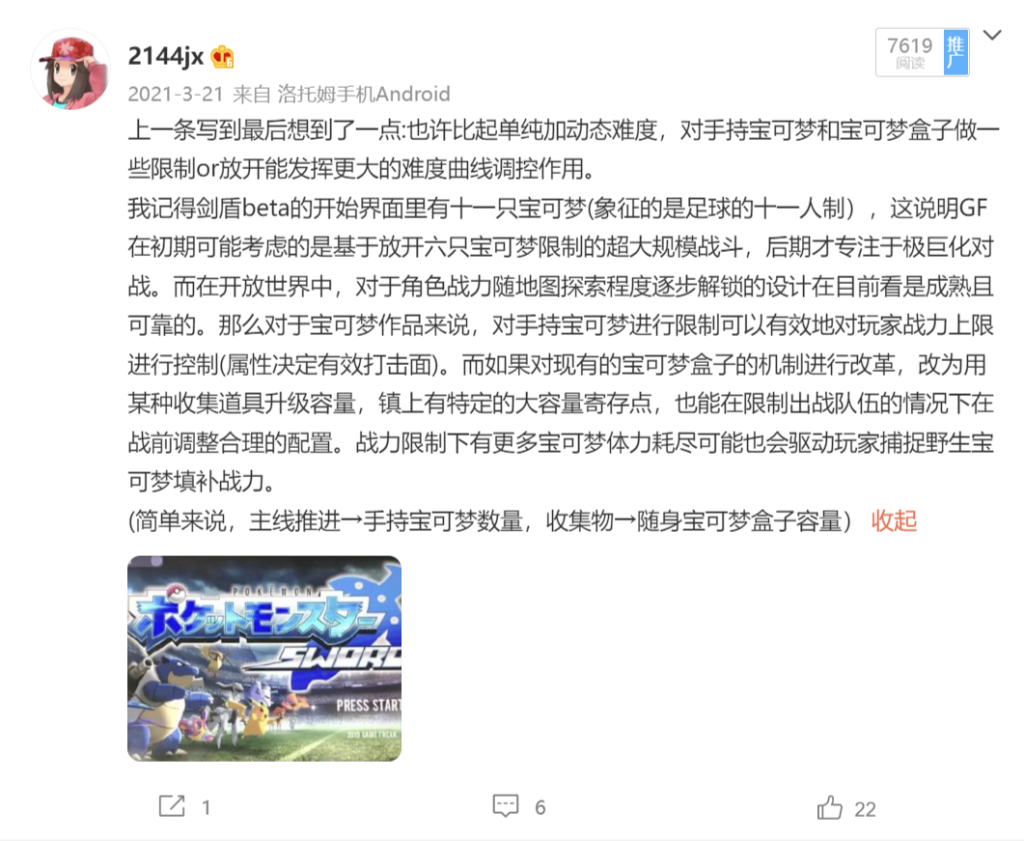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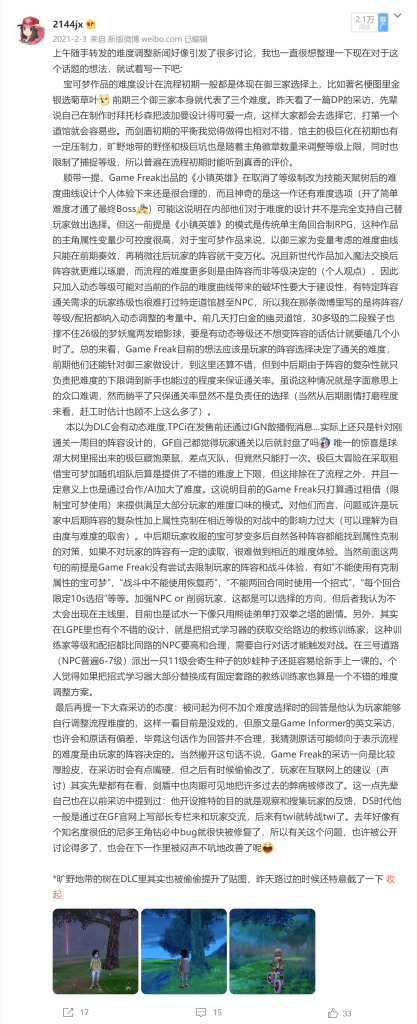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远藤先生在此举的一个例子确实足够生动形象。
远藤:
是的。毕竟,你们听说过,哪个真正让人信服的,“绝对需要它”的理由吗?
比如说,玩“数独”这个铅笔解密游戏的人,大多数会反复尝试相同难度的问题。但是,问他们会不会厌倦,答案是NO。至于为什么他们不挑战高难度的问题,单纯因为“那样不好玩”。其实,我认为只有一小部分的玩家,喜欢高难度的游戏。
这个例子或许能够明了地解释为何难度不会随着系列作品推出而提升,而下降的难度设计一部分来源于移动市场的冲击,一些新玩家不愿意在卡关后学习相对复杂的属性相克机制和技能配招(这一点每个知名系列的制作组都会有内部数据去做参考),因此正统系列近年一直致力于降低培育的难度和对战的门槛,对战向的新宝可梦设计也偏向定位明确,简单粗暴,方便新手跳坑。
我认为真正的转折点可能在于GAME FREAK基于机器学习or深度学习做出了真正玩家级别的对战AI,可惜现在学界对此的研究也基本没有找出很好的方向。如果能实现的话,那么此时的野怪和NPC的可玩度就能完全上升几个档次,并且启动界面处的分级的难度设计也相对可行,宝可梦单机对战部分的潜力就能被充分挖掘出来了。
(完)